自W到高C夹枕头:皇上御花园HLH-重新认识中国女性|婚姻,古代传统家庭再生产的根本之道
美国汉学家、人类学家葛希芝其著作《中国“马达”》中描述婚姻时用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婚姻是传统家庭再生产的根本之道,婚姻的本质就是一桩充满利益考量的生意。书中对婚姻中以嫁妆和聘礼为主的经济往来做了考察和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对女性的价值评判,以及这种价值评判背后有着怎样的家庭经济需求。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与中信书店Xmind共同发起的“重新认识中国女性历史”系列沙龙,邀请本书译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系副教授马丹丹,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张佩国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刁统菊一起围绕《中国“马达”》(以下简称《马达》),展开一场关于婚姻与经济逻辑的精彩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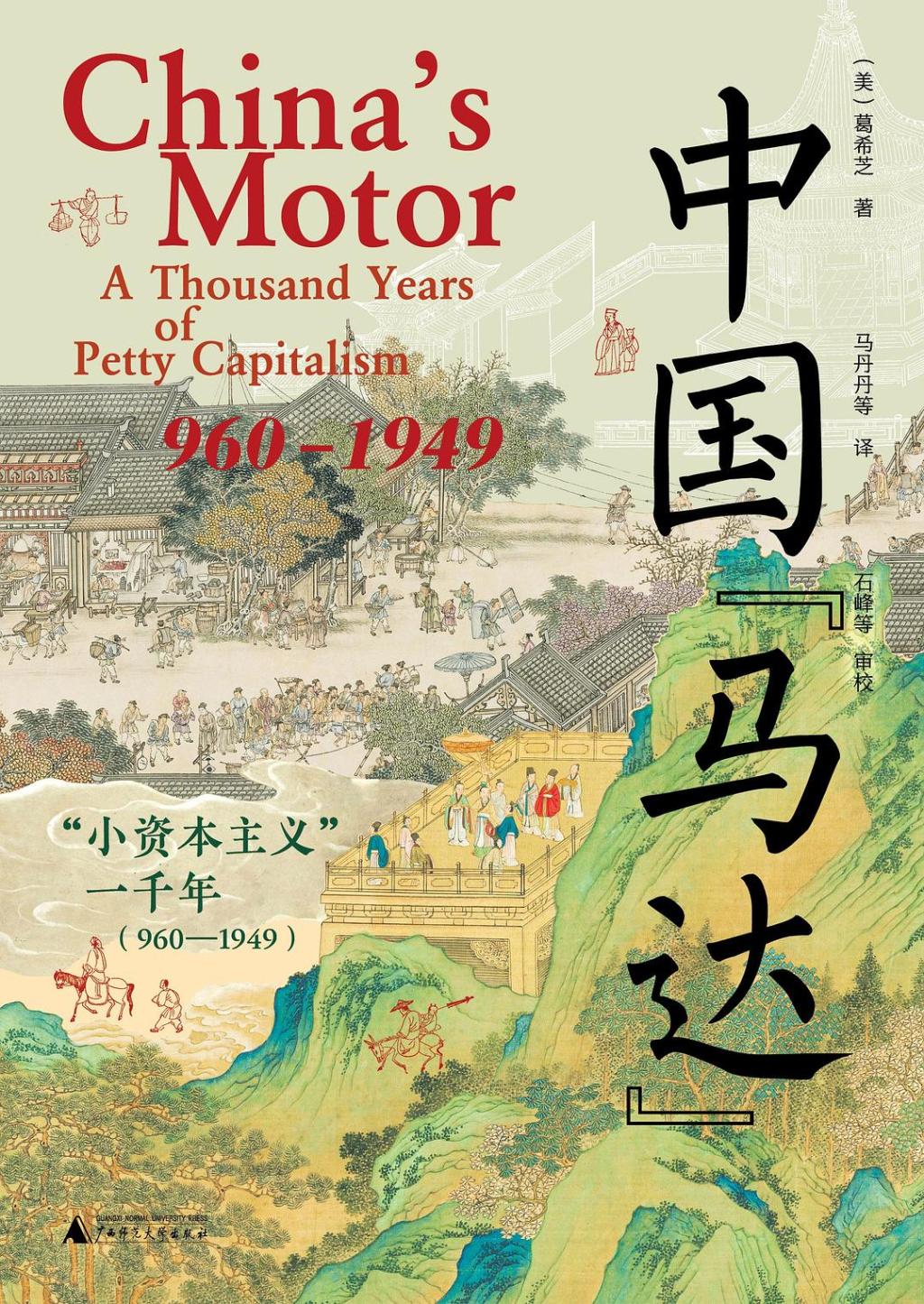
《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
刁统菊:《马达》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包括偏重嫁妆的婚姻,偏重聘礼的婚姻,以及偏重聘礼发展到极致后的买卖婚姻,当然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婚姻,比如女方自幼进入公婆家生活的“童养媳婚”、女方婚礼后回到娘家生活的“缓落夫家”等。可否请马丹丹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种婚姻形式,以及它们的社会背景?
马丹丹:《马达》一部关联性非常强的书,当我们提问有哪几种婚姻方式时,你不得不从空间开始考虑。葛希芝提出一个分类框架,以贡赋制与“小资本主义”的强弱关系为依据,实际上是王朝国家与市场这样两个变量,当然市场化水平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根据它们的复杂博弈关系区分了四个空间。婚姻形式就散布在对应的坐标系上,以偏重嫁妆的和偏重聘礼的两种大婚为主。在两种大婚之外,葛希芝讨论了很多变体,这些变体也放在那个坐标系里,例如入赘婚,小婚(也可以翻译成“童养媳婚”)和缓落夫家(delayed transfer marriage)。具体来讲:
华北平原和四川盆地(强贡赋制生产方式/弱“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地区表现为贡赋制对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在婚姻制度方面,普遍实行重嫁妆的“大婚”模式,严格遵循传统礼仪规范,反映出较强的礼制约束力。
长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强贡赋制生产方式/强“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区域是贡赋制与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两极分化也较大。婚姻模式呈现重彩礼特征,女方家庭往往索取高额聘礼;入赘婚较为常见。葛希芝提到,有些地方上门女婿完成生育任务后,就会被赶出去;珠江三角洲地区盛行“缓落夫家”的婚俗。
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弱贡赋制生产方式/强“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里贡赋制薄弱,小资本主义发达。婚姻形式呈现多元化特征,买卖婚、小婚等模式普遍存在。19世纪台湾因茶叶、樟脑业发展,小婚就这样流行开来。
大新月形地区(弱贡赋制生产方式/弱“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帝国版图中汉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商品经济与政府控制力均较弱。婚姻制度注重亲属关系维系。该区域因属少数民族聚居区,未被纳入葛希芝的主要研究范围。我以为以上这四种分类可以笼统地看作“理想型”,涉及国家与市场两个变量变化下区域发展与婚姻模式的适配性。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最初由当时尚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张佩国教授策划。2016年10月受张教授之邀,葛希芝第一次来上海大学和翻译团队会晤,她抛出这个婚姻理论模型后,我们的一位博士生提出疑问,说与其理论模型相反,如今华北乡村地区盛行偏重聘礼的婚姻,娶媳妇要付出高昂彩礼,常常要把男方家底掏空,有多少新人是在彩礼的谈判桌上谈崩的啊。葛希芝迟疑片刻,然后用不甚流利的中文说:“我的理论不奏效。”这个回应让人忍俊不禁。而今走过漫长的翻译之路,我想说的是,这一理论更接近统计学意义的总体形态,当你拿着这个坐标系锚定微观层面的个体差异,可能就对不上号了。日常生活的散漫性和个体实践的随机性,可能使具体案例偏离理论模型的任一象限。而该理论模型珍贵的价值在于它将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具体的劳动分类,与婚姻结合起来。我在想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执着”地做呢?根据我对该书的理解,我想可能是葛希芝将婚姻看作是生产方式的延伸,女人的劳动价值和生育价值都在国家与市场的复杂互动中被重估和重构,然后做出相应的制度性婚姻安排,这是一种经济理性,还是一种文化理性?我认为是综合考虑的结果。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个体就好像是制度理性的写照,就像《马达》里所说,她被打包进花轿里抬走,她就像一个活行李或者活物件,她是财产的一部分,她的归属解释权属于制度!在履行婚姻仪式的时候,新娘的尊严在偏重嫁妆的婚姻里放在仪式的高位,书里写道,澳门一位新娘因为娘家的陪嫁单子里忘了新妇烧第一顿饭的柴火,她把带来的整批绢烧了当柴火,她的父亲得悉后反而很高兴,次日让苦力抬大捆柴火送到女儿婆家,把婆家的柴房都堆满了。书里还写道,缓落夫家的新娘大婚之日牙口不沾婆家的吃食,食物暗含婆家对自己的所有权的威胁。不过我在惠安材料里发现长住娘家的大婚规矩是饿三天,有一位新娘一想到自己次日起要饿三天,便哭了起来。
刁统菊:刚刚我们讲到了几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在书中,它们被看作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产物。书中提出,“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与国家运作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张佩国老师是历史学领域的专家,请您谈一下,这两种生产方式有何特点,在传统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二者在历史中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张佩国:贡赋制的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葛希芝在《马达》里边讲,它们有矛盾的一面。她形象地说,这就像一段糟糕的婚姻,农民、商人、小业主,他们追求财富的冲动和实践,和我们原来在革命史的维度里所说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对他们超经济的剥削和压榨,这二者很显然存在矛盾。我可以用另外一个很形象的说法,阐明它们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贡赋制的生产方式有一种高度依附性,就像藤条缠绕在一棵大树上,这棵大树就是“贡赋制”,“小资本主义”缠绕在大树上的藤条。所以,“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贡赋制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辩证的。它们相互依存,又有一种反抗性,或者说它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
刁统菊:我对书里面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葛希芝说“国家和亲族长辈们的共谋对商品化的劳动力实现了剥削和控制,这是理解中国亲属关系的核心”。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张佩国:葛希芝在书中大致是说王朝官员们和家族长辈们合谋来压榨剥削普通的劳动者。家族伦理里的“孝”和中国传统政治伦理里的“忠”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
比如说一个宗族祠堂要立一块碑,把家法族规刻在碑上,一般要报地方知县去批准,这显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家国一体。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叫家族伦理本位。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其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家族伦理本位。若家族中的父家长打骂不孝子,甚至于打死不孝子,不仅无罪,而且会获得官府的嘉奖。相反,不孝属于“十恶不赦”里的十恶之首,不要说是辱骂,即使是忤逆父家长都不行。当然每个朝代的律例不一样。从这一方面来说,王朝国家通过官僚体系和父家长从制度上、从意识形态上合谋来强化对于家族成员也好,或者劳动者也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剥削和压榨。
那么,要理解贡赋制体制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亲属关系的核心就是要看到王朝国家官僚体系和父家长怎么合谋来压榨家族成员,这是这个问题的一面。另外一面,我们来理解中国“马达”的两种生产方式,刚才讲的那种矛盾的状态,它如何形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则必须落实到亲属关系上面,比如今天我们的主题——婚姻关系,这是相当重要的。

沙龙现场
刁统菊:这本书在导论中强调,试图揭示隐藏在表面看起来变动不居的近现代中国生活中的宏观结构中的连续性,探讨帝制中国晚期和当代中国有什么文化相通之处。同时,她也注重追求解释“连续性”,而非传统—现代的对立。
我一直觉得很好奇,父权制宗族制度是怎样跨越几千年走到21世纪的?以至于女性也在为这个制度做贡献。从周代青铜器上的祭祖记载,到今天,一些大规模的祭祖仪式上才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这本书告诉我,无论是贡赋制,还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需要这种文化制度。第六章提到传统的宗族文化是贡赋制建构的结果,反过来,建设宗族的目的之一也是实现贡赋制亲属关系。
那么,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怎样影响传统婚姻观念的?本书的作者葛希芝在书中说,中国历史中相对稳定的一致性让中国人能够“从历史长河中辨认其文化传统”,在两位老师看来,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婚姻观念是否体现了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呢?这种观念在当今社会中又是否得到了部分延续?
马丹丹:葛希芝用一个多样化的丰富笔触描述了婚姻当中的“二重性”,她告诉我们,与“小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婚姻居然是可协商的。
当我们谈到直接嫁妆和间接嫁妆的时候,它揭示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策略,那就是母亲把女儿嫁走,从男方那里拿到一笔丰厚聘礼,除了把它再返回给小家庭,她可能还会留一笔钱。这笔钱,这个母亲可能会用于投资借贷,参加民间标会,活跃她的金融。她不想把所有的嫁妆返还给女儿,因为这些会充公,成为贡赋制的一部分,婆婆会觊觎。所以她会留项链、首饰——通常是黄金打造的,这些是给她女儿的,这部分在她女儿急需的时候是可以变现的,可以说这是母亲给女儿的一点点小私心。
另外一个就是私房钱,葛希芝说私房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中男人的钱是老婆的钱,但是老婆的钱是老婆自己的钱,所以这个媳妇会用很多小心思,留住自己手里的钱,她们有很多种活络的手段和方法实现“钱生钱”。女性将自身的可协商性融入婚姻实践,并在策略运用中发挥到极致。
另外一种更极端的是买卖婚姻。买媳妇卖媳妇,谈媳妇的价钱就像谈市场里的货物一样。她引用武雅士(Arthur Wolf)采集的俚语:买个媳妇就像是“卖到市场上的猪”。因为猪是农产品当中的高阶产品,买个媳妇金贵到跟买猪一样。
妇女的价格还表现出经济规律的涨幅,所谓“随行就市”。这些“买卖经”是对女性高度的物化,物化的背后是讨价还价的商品经济在婚姻当中的折射。葛希芝说她不同意杰克·古迪很含蓄地去谈中国的聘礼,半吐半露地描述聘礼不是卖女儿,其中有礼仪的美好寓意。小资本主义在婚姻的体面之下发挥着灵活协商作用。
张佩国:婚姻关系的实际面相有很多,嫁妆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我们俗话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父权制的家长对于婚姻关系缔结的父权制。或者用葛希芝的话说,它实际上是有贡赋制的支配性在里面。
嫁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女方家长的一个父权制物化的形式。江南一带的地方志有一个民俗上的说法,把出嫁女污名化,比喻成赔钱货。明清时期盛行“赔钱货”的说法,这是因为江南棉纺织业、蚕丝业比较发达,这种劳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里面,主要的劳动力是出嫁之前的女儿,所以对女方家长来说,女儿出嫁了,家庭丧失了从事副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劳动力,而且要赔上一笔嫁妆。这个买卖,显然是赔钱的买卖,所以把出嫁女称为赔钱货。

漳缎织机 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马达》里讲夫妻关系用了一个谚语:官员的印把子和商人的钱箱子,它们都掌握在谁手里呢?是掌握在官员和商人的老婆的手里。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商人都怕老婆,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妇女在整个家庭理财当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个方面,这种现象足以颠覆传统的贡赋体制、父权制的这种婚姻关系吗?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就因此而提高了吗?显然不是这样。所以这种矛盾的现象还必须放到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样一种比较纠结的矛盾关系当中来看。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变体。比如童养媳婚、入赘婚等。入赘婚在不同的区域,所表现的对传统发明的形式不一样。比如说书中引用的福建地方材料,说福建的商人在木帆船的时代,哪怕有三个儿子,都不一定舍得让自己的儿子随船去远航;往往是先招贫苦人家的儿子做养子,代商人行使在船上的管理权力,比如让养子做伙长,剩下那些相对技术性比较强的人做大副等,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觉得考察合格,再把养子招为女婿。这实际上是一种父权制和“小资本主义”商业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案例。
刁统菊:我们在书里还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贡赋制主导的偏嫁妆的婚姻形式,但是由于“小资本主义”的介入,婚俗出现了非常多的、非常强的可协调性,或者叫可塑性。《马达》里列举了很多作者的田野观察以及民族志材料来讲婚俗的可调塑性。实际上,还有很多社会风俗也受到经济关系的影响。这种“小资本主义”的影响在社会的哪些方面有所体现?可否请两位老师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明一下。
张佩国:“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把它更具象化一些,像书中讲述的“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私有化的一个生产体系,包括农民开豆腐作坊、手工业者开工匠坊等。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劳动人民,都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边的成员,他们的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我们今天讲的股份制,在商业史的研究中发现,其实很早就存在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家族的形式。如曾小萍研究的自贡商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贡商人主要从事的是盐业,盐虽然说是国家专卖,但是在具体的盐业生产当中,专卖指的是其销售市场这一面,盐的生产,从盐场的角度来说,还是要落实到家户或者家族。从中山大学黄国信教授的学术团队对华南灶户盐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家户以及家户之间,是如何投入生产成本,怎么来分红。他们实际上都是按照股和份——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是不完全一样的。再比如郑振满教授他们研究的福建宗族里边对于商业的经营和占有,实际上也是股份制。
商业是一个方面,“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中的农田水利灌溉,是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料。一个地方对水利工程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基本上也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单位的。比如说在明清时代,横跨广东南海县和顺德县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叫桑园围。桑园围总共有14个堡,11个堡在南海县,3个堡在顺德县,这种合作也是宗族与宗族之间的联合。科大卫在《皇帝和祖宗》中重点研究了桑园围的案例。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话说,宗族做生意来了。所以这些手工业,很多其实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的。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这些实践,实际上离不开所谓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王朝国家官僚体系。比如说官窑的生产管理还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比如说清代中期改贱归良之前的匠人,他们的户籍都叫匠籍,匠籍某种意义上其实带有贱民等级的意义。基本上他们都是以家户、家族为单位的。所以农业、手工业、商业这一系列的劳动实践的过程,体现了家族主义、父权制和王朝国家在管理生产上的一种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亲属关系连接了贡赋制的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刁统菊:张老师提到,在“小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家庭、家族可以被看作一种经济组织。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联合,比如说通过婚姻建立两姓之好。在“小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婚姻中,女性面临着经济价值的衡量。那么,两位老师觉得,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女性与家庭乃至宗族的关系是怎样的?
马丹丹:葛希芝说贡赋制控制“小资本主义”,不是通过税收,而是通过亲属关系,其中,女性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小资本主义”背景下,女性与家庭、宗族的关系复杂且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与当时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紧密相连。
在“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女性作为姊妹和女儿通常没有财产权,但女性却是小资本主义的重要生产力,这是不是很矛盾?女性对嫁妆没有“死前继承”权,即嫁妆的继承权在父母死前不生效。不过也有陪嫁清单里赠予土地的罕见例子,土地以象征的形式被封在盒子里,手捧着走在陪嫁队伍里。
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买卖和继承都与男性紧密相关,女性被排除在外。而且嫁到婆家的地位不稳定。都说“母以子贵”,但实际上母亲连孩子的所有权都不一定保得住。那这样是否意味着女性一无所有呢?2019年我在斯坦福“小红楼”访谈葛希芝的时候,她说女性并不决然是牺牲品,她们拥有的是口舌的力量——“骂街”。《马达》里面引用庄士敦在山东威海卫的观察,一个女人在街头咒骂,咒骂的声音可以传出两条街。
在处理惠安材料的时候,葛希芝提醒我,谁养活她(Who feed her)?谁控制她的劳动?在纺织业等行业中,女性的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然而她们的劳动成果却常被男性亲属掌控。例如,宋代纺织品生产规模庞大,女性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社会控制她的方式却是缠足。缠足与商品经济咬合,形成一种强制制度,通常是母亲给女孩缠足,理由却是“缠足才能嫁得好”“大脚女人没人要”。正是女性劳动与商品化的羁绊构成了葛希芝从女性劳动切入连续两章(第五章、第六章)讨论宗族的阳面和阴面等形形色色反差与对照,也包含对高彦颐的缠足与性的意义再生产的性别理论的商榷。
二重性生产方式本质上是贡赋制与小资本主义对剩余(surplus)的争夺,这一思想沿袭了沃尔夫(Eric Wolf)从剩余切入讨论支配权、代理人与农民战争的经典思路,葛希芝发现小资本主义以“作为合约的家”的方式集结起来,与贡赋制竞争剩余。可是竞争又是在支配的框架下进行,即作为法律/法人概念的宗族的发展。这是和四个大区分类相匹配的宗族类型的变化,根据祖产、产业经营获取利润的程度分为类型I、类型II、类型III。类型II既然产业稀薄,就把有限资源投资在子弟读书上面,将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这似乎解释为何山东等华北省份仍旧是“考公”竞争激烈的地带。由此宗族兼具父系血缘(patrilineal)与公司(corporation)的双重特征。宗族既是向贡赋制输送剩余的毛细血管,又开发出躲避贡赋制压榨财富的诸多手段,例如华北的富商把财富埋入地下,乱世时还会置换成门口摆的石墩。例如经济最富庶、斗争最激烈的长江流域,宗族以兴修祠堂、宗庙的方式避税。
如果说以上还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载体的细化,里面包裹了亲族制生产方式(kin-ordered mode)的内核,那么性别和性别劳动成为葛希芝撬动沃尔夫理论杠杆的支点。沃尔夫只是将性别放在社会关系集结当中一个次属存在,甚至是亲族生产方式中听从男性支配的一个劳动分工结果。葛希芝挖掘了性别劳动发挥的动力机制对于二重性生产方式的认识论价值。她发现,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女性从属地位的确立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作为悖论的强调贞洁和妇德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包抄围剿开来,反讽的是,狐狸精的传说对朱熹“假道学”的攻击与挪揄不知道逗乐了几代妇女。在访谈中,她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不仅体现在宏伟历史的书写中,也体现在女性的纺纱中”。用书里的原话,“虽然贡赋制与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继续‘斗争’,但为了争取对剩余的控制权,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实践都仍然牢固地建立在妇女的依附地位之上。”(第83页)
张佩国: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提及妇女在家族当中的作用、角色的时候,很有洞察力地讲了一句话:妇女是连接各个宗族的,包括祭祖本身,虽然妇女不能进祠堂,但是在以家户为单位以及以五服为单位的小亲族范围祭祖的时候,妇女是祭祀仪式的主角。
葛希芝也引用过武雅士在福建调查田野笔记中关于当地妇女的一个说法,说男人有男人的祠堂,女人有女人的庙会。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从祠堂宗族的研究来说,妇女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她们的声音是被遮蔽的,但是赶庙会的人主要是妇女,所以要是研究宗族和民间信仰之间这样的一些关系的时候,可能妇女的角色是突出的。
回到婚姻关系与宗族家族制度的议题上,葛希芝也引用了卢蕙馨的“子宫家族”概念。“子宫家族”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在父权家庭荫蔽下,以母亲身份的女性为中心而形成的家庭。现在家庭社会学的母职概念,我想它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能是从卢蕙馨的“子宫家族”中来的。对于子女的亲情,母亲的呵护、慈爱,实际上缓解了父权制家庭对于家族成员的一种压榨。
但是葛希芝教授引了这个话以后,在做相关讨论的时候,说尽管母亲有子宫家庭的这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她仍然逃脱不了父权制的支配之网。所以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在整个传统中国的“二重生产方式”中女性的这种主体性反抗。
刁统菊:刚才马老师提到女性与商品化的羁绊,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婚姻形式,我就突然想到葛老师在书中提到的“缓落夫家”以及保持独身的女性,想请老师们谈谈,她们的生存处境是怎样的?她们是基于什么考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这种现象是否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权力?
马丹丹:葛希芝在《马达》中引用了斯托卡德(Janice Storkard)的自梳女研究,她是武雅士的学生,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的美国学者。她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缓落夫家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女人们在缫丝业发达时期拖延去夫家的时间,后干脆不嫁,成为自梳女。这种抗婚形式即使在缫丝业衰落后还存在着。缫丝业的劳动需求,让女儿选择成为自梳女,并彻底断绝了其为夫家生儿育女的婚姻负担,这使她们可以更加顺畅地投入缫丝业生产。缫丝业推动了自梳女群体的经济独立,改变了世俗对抗婚的污名化。缓落夫家以及从缓落夫家衍生出其他形式抗婚形式的女人们,其实也再创造着她们的身份选择,无论是自梳女,还是给丈夫买“妹仔”(替身)以代替自己和丈夫结婚、并换得自由身的女人,还是为了牌位到了老的时候或者快死的时候才回到夫家的女人,她们均在不同程度地表达对婚姻的抵抗,有的甚至采用自杀的方式。但是这些抗婚实践又不是绝对的反抗(resistance),还包含着当地文化的接纳与延伸、妥协与同意,称为柔化的“反婚姻实践”可能更加准确。在当地风俗中,缓落夫家并非是低等的、被人看不起的婚姻;与之相反,一个新娘如果迫不及待地和丈夫住在一起,才是被人看不起。自梳女被原生家庭排斥,依靠姐妹自助维系群体团结。当失去劳动力的时候,她们会用私人财产或“凑份子”买一块地方修建名为姑婆屋(自梳女终老互助的居所)的集体住所,由下一代姊妹们或养女为她养老送终。姑婆屋与她们小时候生活过的姐妹屋相呼应,差异在于前者有私人产权。姑婆屋建在飞地之上,它是在原生家庭、宗族和乡村的缝隙中开拓的临界位置。

斯托卡德是较早关注冥婚(ghost marriage)的海外学者之一,女人在孤魂野鬼的世界寻找归属也成为抗婚的一种方式。活着的“新娘女儿”嫁给鬼丈夫。嫁给快要病死的丈夫,虽然坐绿骄子进门,但是新娘要参加丈夫的丧葬仪式,为丈夫哀悼,这是一种较高等级的婚姻模式;抱着丈夫的牌位嫁进门,不参加丈夫的丧葬仪式,被看作是“低等的”婚礼模式。冥婚是“缓落夫家”婚俗的折射,它是那些更多的回不到“姑婆屋”社团、又无法通过“赔偿婚”为自己的身后事未雨绸缪、同时又不允许死在家里的女人们,在彼岸世界给自己安排的一个着落。
回到《马达》,葛希芝对独身女性的描写充满了诙谐、愉快和明快的氛围。当然,她大量地依赖二手材料向那些保持贞洁或拒绝被婚姻奴役的独身女性的自主生活投来欣赏一瞥。容纳独身女性的当然是当地的斋堂和庵堂。她们以“天足”装束出入庵堂与人家的法事之间,抛头露面,四处化缘筹资,尼姑们在空地上野餐甚至有点英国女学生下午茶的范儿。她们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心宽体胖,掌握经济独立的手艺,如采茶、刺绣、缝纫。不过这里面也藏污纳垢,小女孩被卖进尼姑庵按照艺妓的标准养起,或收留长居妇女,暗含性服务的暧昧。书里引用了刘鹗的《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到第六回,被林语堂改写成英文《泰山的尼姑》。小说里的年轻道姑逸云被葛希芝称为“女英雄”,实际是在算计与权衡后做出独身的决定。
刁统菊:刚才马老师提到“孤魂野鬼”这四个字,一个已嫁的女性,如果不生育,就没有办法进入父权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哪怕这个孩子不是她生的,记在她名下,她也可以进入这个体系,在死后可以享祀。因为她在娘家属于暂住者,娘家不算她的终极归宿,要不然她就是孤魂野鬼,所以这本书里面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也揭示了民间信仰和现实经济关系的紧密联系,比如说神鬼形象映射现实利益纠葛。能不能请张老师谈一谈,传统社会中的这种婚姻、男女关系催生了哪些民间信仰和民间风俗;在当代社会,这些民间信仰和民间风俗是否还存在着,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张佩国:倒不一定是从婚俗的角度来谈,因为葛希芝教授这本书的这两章,是围绕着民间意识形态来展开的,其中一章叫“民间意识形态:统治者和老百姓”,另外一章“民间意识形态:男人和女人”。民间意识形态的这个概念是1987年,葛希芝教授和Robert Welle共同在Modern China这本期刊上面发了一个专号,是关于民俗的或者民间意识形态的一个研究,实际上就像“民间意识形态:统治者和老百姓”这章的内容一样,民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民间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间意识形态是整个传统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识形态。
葛希芝教授其中用了一个比喻:民间意识形态里边连接统治者和老百姓的是什么呢?是钱。民间信仰中的宗族祭祖,无论在葬礼还是祭礼当中都是要烧大量的纸钱的,烧纸钱的这种仪式,在老百姓民间的观念里边,实际上是送给阎罗殿里各位神鬼的钱——上至阎王到判官再到无常鬼,使他们的这个祖先到了阴间的时候,在投胎的时候免受酷刑。
老百姓认为烧纸钱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超自然世界的那些神明也好,鬼神也好,不是腐败,不是行贿。只要他们的祖先能够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好的去处,并且反过来说会保佑子孙,他们就觉得得到了回报。
在一个物质世界里面,神鬼祖先,借用武雅士的解释,神相当于现实世界里的官员、皇帝,有些是死后化为了神,比如说关公;鬼主要是指那些土匪、乞丐、郎中,这些流动的人群,他们对一个农业社区,对农民来说,是外来人,是陌生人,是一个危险的力量,因为死后没有后代祭祀他们;祖先对于一个人来说或者一个家族来说,是自己的祖先。这三者之间在超自然世界里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很机械的,而是物质世界、现实世界在自然世界的一个投射。
葛希芝研究民间意识形态,虽然也是研究文化的,但是她很注重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把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祭祖的仪式,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脉络中。比如说宗族家族制度必须放在科大卫教授所说的礼仪革命,从宋代到明代,怎么来造宗族的这样一个历史政治经济的进程当中,来理解中国人的民间信仰。
同样,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在民间意识形态上也体现了几个面向。书中讲了女性的神明,比如说天后。哈佛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对此有专门研究,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神明的标准化》。天后的信仰按照葛希芝的理论来说,实际上是贡赋制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有机结合。
民间意识形态里边有一些信仰,可能不完全是像关公信仰、天后信仰那么具有正统性的。比如说碧霞元君的信仰,碧霞元君又叫泰山奶奶,所以它某种意义上带有送子的功能,所以很多妇女尤其已婚妇女会去泰山社拜泰山奶奶求子,叶涛教授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求子还愿的时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农商文明里的妇女,虽然对家庭做了很大的贡献,虽然有所谓的私房钱,但是可支配的财富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去还愿的时候只能塑一个泥娃娃,或者拿几个红鸡蛋。当然这是整个宗族的地方社区的一个合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民间意识形态当中妇女的这种信仰,也恰恰和妇女在整个现实世界、世俗世界当中的社会地位是相关的。
马丹丹:民间信仰和市场逻辑是一致的,即讨价还价。葛希芝把老百姓对待官僚的一套逻辑用在民间宗教当中,最接近官僚形象的是大小神祇,这让人联想到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不过,老百姓对待官僚的方式在葛希芝的笔下更加接近小资本主义在民间宗教流通的弹性与活力,在贡品上与神讨价还价。《马达》里有一个很犀利的说法,统治阶级以慈爱、仁慈的形象向民间灌输,但统治阶级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拿走具体的东西而只归还抽象的事物”,老百姓知道还是要靠家户劳动,供养大小官僚,从贡赋制收割机一般的麦浪掳掠中保住几颗麦穗。老百姓发明了他们的民间宗教,它鼓励平等交易、互惠道义的属人世界,它在阴间也臣服于“土地爷开银行——钱通神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魔力。这意味着民间宗教既是世俗世界等级制的投射,同时又是颠倒、变形和翻转的秩序重构。葛希芝在台湾地区开展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老百姓形容说最好让神待在办公室,我请它来的时候它再来,平常就不要动了。这是一种对神很矛盾的心理,可是很真实。还有一种说法,把庙修得好,神才愿意住进去。神的等级几乎是官僚制的摹刻。土地公公看上去慈眉善目,实际是警察或衙役,趁职务之便伺机索要贿赂。土地公的恶事让土地婆背黑锅,土地婆据说是结婚后变坏的。灶神,不把他的嘴用麦芽糖粘上,他不会“上天言好事”。
与小资本主义的金钱观相关联的是祭祀的商品化程度差异。华北地区贡赋制较强,当地民众在祭祀时,仍偏爱焚烧银锭作为祭品(money for the gods)。元宝非常有贡赋制的象征意义;而在发达的东南地区,人们用的是各种纸钱。纸钱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意义。例如潮州“斋戒娘娘”通过背诵佛经赚取冥钱,念很多遍佛经才能挣100个铜钱,这也叫功德钱(merit-money),等她们死后到达阴间才能返回,存在阴间赵公明开的“钱庄”里还会生利息。
从民间宗教延伸到男人和女人,小资本主义的可协商性与生产性在女性神明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发现女性神是平等的、博爱的,与注重等级和地位的神不同,后者通常要求举社区之力为其重塑金身、打造庙宇,耗资不菲,女性神明索要的贡品微薄,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给个红鸡蛋、塑个泥娃娃,还有敬献红绳的,系在神像怀抱的婴儿的脖子上。葛希芝在山西庙宇的田野考察发现,当地老妇人无钱装修庙宇天花板,用自己绣的花布来装饰。女性神明天然地唤起命运的共情和姊妹互助。台湾的妓女祭拜那些夭折的女孩的孤魂,送上小鞋,仿佛她们的被遗弃感得到了抚慰。有些庙宇角落还会有纸牌位,当地妇女以此纪念那些难产而死的妇女。女性神并不贪婪并不说明女性神都视金钱为粪土。广州的观音庙还会涉足金融借贷,借贷对象均为底层手工业者,当地居民认为,能从观音那里借来资本,他们肯定会走财运。






